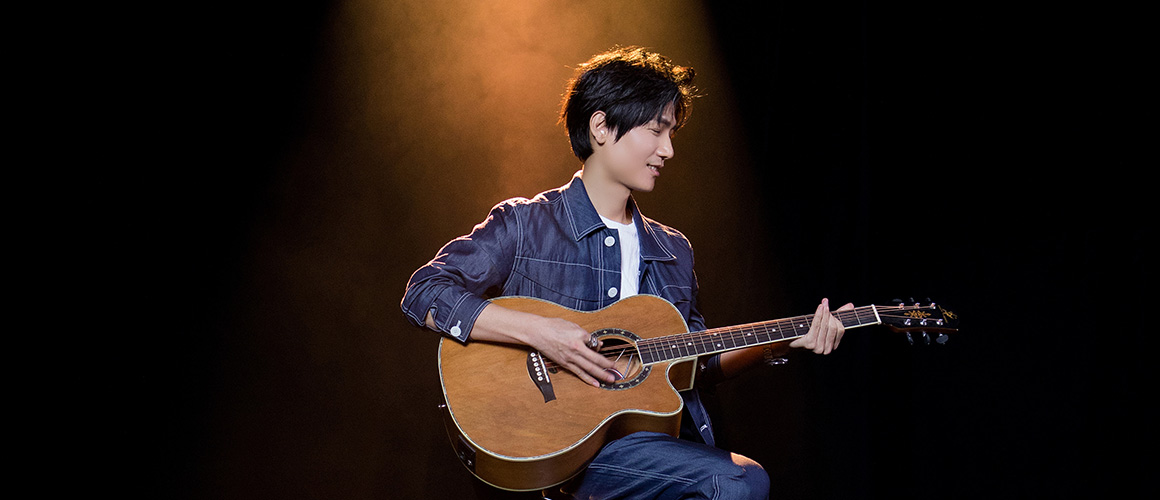《守》四(20cmX30cm) 布面油画 2013 王怡

《守》六(30cmX30cm) 布面油画 2013 王怡

斯蒂文·霍尔的建筑作品西雅图大学圣.依纳爵教堂(Seattle University Church of St. Ignatius)与王怡的《守》系列四、六的定格、镜像锚定和现象学对比研究
霍尔定格了一个“自由选择中心”的镜头:“今天因为’分散的以及负面的能量消解 ’带来的艰苦经验,与随时消灭的印象同时存在。当一个人抬头望向纽约中央车站大厅拱顶的那一刻,光线从布满灰尘的梁间、从巨大的拱形窗倾斜而下的那一瞬,一个人的知觉改变其意识,人的关注会被拓宽,时间也扩张开来…… ”(“霍尔说:当代的文化及现代的方法“,以下的“霍尔说”皆为引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博士Almagor 《霍尔说》的系列文章)霍尔建筑中定格“自由选择中心”的镜头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出现,当我抬头看霍尔在北京东直门设计的8楼相连的“当代MOMA”时,在大面积冷峻的立面中,某一个窗格或体块底部的多种色系序列通过内部灯光丰富的交融,让你的视觉不断定格于你的”眼睛所截图的”部位,强求平淡之中包含的精巧形式和内容,这种“繁复的纯粹性”存在着学术思维内在逻辑的“召唤效应”,召唤的动因就是王怡的一系列的画面。比如王怡在《守》系列之四、六两幅作品中对窗口内繁复的现象交融的定格所营造出的“纯粹的繁复”。这种表达在史蒂文·霍尔的作品成都来福士广场中直接把建筑立面作为油画画面的视觉机制来呈现——直接把例如王怡《守》系列的窗格内的日常情景的繁复性翻译成抽象的线性视觉代码。霍尔聘请了一位建筑师好友Lebbeus Woods 来独立设计这这个窗格 (Woods是美国老牌的建筑艺术家和建筑画家,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建成的实际项目,他拥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和机会,却仍旧执着于画笔。或许,建筑对于他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绘制式理想国,一旦与世俗接壤,就失去了它的神圣与纯洁。他的建筑绘画曾经影响过两部电影:特里·吉列姆的《十二只猴子》和大卫·芬奇的《异形3》)霍尔让建筑的最终解决方案存在于绘画性的感性实质中,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经验。他让Woods以抽象、交错的装置来表达一种“纯粹的繁复”为成都的一个大型多功能混合建筑群体设计一个窗格(窗格里隐含着回廊与亭子)。这是一个高高耸立的由互相交叉的桥梁和坡道组成的建筑结构,它是Woods先生建筑构想的一次具体落实:一个密集的皮拉内西(Giambattista Piranesi,18世纪末意大利观念性的建筑师、视觉艺术家)式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爬到顶端俯视新中国的都市蔓延景象。在成都来福士广场所设计的绝对理性的方格网大楼中以异形雕塑作为破解,并形成了新的对话,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批判性空间介入,概念传达一目了然。库哈斯在美国伊利诺理工学院挑战密斯设计的经典透明盒子的案例也堪称一种空间介入的典型,原本完整的理性秩序被曲型建筑和斜线分割消解开来,一如王怡在2014年的作品《依》中用黢黑的头发挑战大面积轻质透明的背景,如同霍尔用大量接近虚无白色或基调轻盈的建筑体量来消极空间的存在。而成都来福士广场Woods窗格与整个建筑的呼应效果并不是为了取得皆大欢喜的效果,而是制造王怡常说的“画面矛盾”,以矛盾为介入手段,以平衡术作为对话的方式,让设计者以一种姿态的介入成为矛盾核心,传递了建筑师个人的观念基因。这就是霍尔所说的意图:“用强烈的现象属性完成空间,将建筑提升到思维的高度”。当你看到大面积的序列的立面是枯燥的,一个窗口制造了”繁复的纯粹机制”便可打破这种单调,王怡的画面就是在不断定格这种“现象区”——每当夜幕降临,成都来福士广场所有的建筑群黑压压一片,首先开启灯光的是Woods哪个大的窗格,这时候的造境是王怡《守》系列一、二、三中的聚焦于大片漆黑区域中的一小簇光源的转译;是《守》系列之四的冷峻的墙中由门窗透出的数点温和的烛光、一片台灯和顶灯的漫射操持视觉力量的胀缩盈亏——放大和缩小;Woods窗格中伸出曲折的线性灯柱,表达的荒芜与重生是《守》之六中一枝绿色植物伸向窗台并与室内宗教感漫反射交融的建筑仿生学;《守》之五中行者的一头白发是移动的灯源,是Woods的灯柱与曲折人行走道的动态同步交错;《守》之七、八(又名《荒》、《落》)中对孤独荒野的叙事和自我诗化,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和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的亮度是黑暗中灯带的换位思考,让人的脑海自然想起“未选择的路”的句子:“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却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同时,《守》又让我想起一个我编译的一个故事:一位读者走近晚年逐渐失明的博尔赫斯,问:“你是博尔赫斯吗?”博尔赫斯说:“有时是吧,尤其是当我夜间走在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时候。”博尔赫斯虽然失明,但他借给我们一个眼光,这个眼光能深入地进入过去的秘密。西川说,“能看见世界的人可能也是个瞎子。博尔赫斯眼睛看不见,但心明眼亮。失明加强了他的洞悉。博尔赫斯把记忆变成对梦的召唤,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王怡的灯簇在黑暗中就是博尔赫斯的眼。一如王怡的自述:“因为生活中总是充斥着矛盾,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用于独处,对我来说,孤独并不是什么坏事,也只有那个时候我的思维才不会被各种因素左右,才能真正感觉到自由,于是可以更加主观的去思考一些东西,阅读一些东西,缓和掉心理上的矛盾,做出一些作品。”王怡孤独的意象常常人迹稀罕的景观,她常常以一个人,一盏灯,一棵树的定格孑然一身的图景;“一”之中还不断分裂单数:一个瑞典街头的转角,一个丝绸垂幕,一堵斑驳的喷漆墙,一抹阴凉的阴影;一个个不断出现的仰视 (端详建筑),不断出现的一个个低头:妙龄的沉思,新上海人低头看手机,瑞典人低头看书......都反映出一种场所激发感官的本质。在“一”位单位的变化中,她的意象形同一棵树的孤独,又如地平线上以一棵树为雕塑的独立。她那带着骨头的孤独视觉是治愈当代中国“热闹的孤独”的一针疗法。

《守——未眠2》(60cmX80cm) 布面油画2015 王怡

成都来福士广场,四川成都, 310,000 ㎡,2010-2012,斯蒂文·霍尔

斯蒂文·霍尔邀请建筑师Lebbeus Woods 来独立设计成都来福士广场的一个窗格与王怡的《守》一、二、三和《守——未眠1、2》的建筑空间的场所精神比较研究
在王怡视觉知识和布面肌理中,以深入繁衍内涵,物质的现象使人的知觉混入色素原料之中, 而精神或心理的现象则围绕人的内在知觉。她表达的“布面建筑”的挑战是在强调现象性经验与表达意义的“同声翻译”;是在激活内在和外在知觉的通约性; 从而展开二元的通感,独立地对环境和场地发出“着色的回声”。霍尔建筑能通过“现象区”(phenomenal zones),提供给使用者全部的经验, 并通过现象影响全部的重要系统。霍尔信奉现代主义思想的建筑,但他又不满于现代主义建筑过于具体和冷酷的表现,这如同王怡以具象批判具象。霍尔强调他的设计目的是在于寻找建筑难以琢磨的本质,这如同爱做家务的王怡有着超强家居空间整理术一样,她对错综复杂和行踪不定的视觉质感的沉迷不已。建筑规模和功能复杂性的增长加剧了建筑朝着抽象化发展的固有倾向。王怡的画也是由高强度或者“负强化”的“感知项目”工作量演化成抽象意义,意念推动无意成为某种形式的现象学,直觉成为这种推动力。

《守》三(62cmX80cm) 布面油画 2013 王怡
建筑现象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汲取的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思想,其建筑设计理论和实践并重。霍尔的作品是建筑现象学理论在当代建筑实践上最充分的再现。霍尔强调的是“场所”在建筑设计中的决定作用,霍尔的建筑中包含了个人经验、建筑本身、场所因素存在的密切联系。一如王怡画面中的建筑是与特定的地点具有密切的关系,不能脱离环境和人的活动论建筑。同时也体认场所与艺术家的个人经验和倾向的关系。王怡的绘画和霍尔的建筑一样,都是与它所存在的特定场所中的经验交织在一起的。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思考去理解世界,即使是受到外部影响,也没有人能走出自己的世界,当王怡画建筑的时候,她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她自己画成建筑。面对场所、环境和建筑必须依靠人们的纯粹的意识、知觉来进行自我关照从而获得个人真实的经验和知性。八十年代,霍尔起草了建筑学文本《锚》,这是他将建筑历史、选址、现象、理念、风格相互融合的第一次宣言。它阐述了一个运筹理念:由于我们在建筑设计中往往遇到不同的选址和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要积极利用那些不可预测的因素,而不是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这个过程也是王怡从选择场所到定格画面的过程,她的定格就是霍尔的“锚”。现象学的潜力在于,作为建筑实践的出发点,它能以更加尖锐的方式面对“生活愈发人工合成化”的现状。现象学的经验能够与新技术兼容,那些技术能够创造新的体验机制。对于霍尔来说,建筑环境里所包含的物理的、心理的、世俗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对于王怡来说,建筑的空间体验同样是一个复杂现实的集合。

《傍晚的面包店》(60cmX80cm) 布面油画2014 王怡

《守——未眠1》(50cmX60cm) 布面油画2014 王怡
王怡画面中的人物是场所的一部分, 人是移动的场所,人通过汇集特定场景的各种意义, 建筑得以超越物质的需要。实质上,这是通过建筑与场地的现象学的、经验的结合而得来的。霍尔将其称为“诗的连环”(Poetic chain)或“形而上学的连环”,也就是他在九十年代年出版的《寻找锚固点》一书中所提出的"将建筑锚固在场所中"——这是描述王怡的定格最生动的语言之一。王怡的画中建筑的锚固点就是作为“内在知觉”(inner perception)的现象(经验)交融在作为“外在知觉”(outer perception)的特定秩序中。霍尔有一部作品集的序也叫《锚定》,王怡对建筑锚定式的记录是一种在真实的现象中进行思维的活动, 对场地的亲身感受和具体的经验与知觉是建筑重述的起点和生成,同时也是画面中的建筑最终所要获得的。画家个人对建筑的真实知觉试图在建筑塑造上创造出一种是人能够亲身体会或引导人们对世界进行感受的契机。那么,建筑所呈现出的现象是如何为人们的知觉所感受的呢?如果将霍尔的建筑对可以为人们的知觉所感受的现象作总结,包括了纠结其中的透视学的空间、色彩透视与光影、定格与时间片断、夜空间(夜间)、细部与声音、作为现象镜头的水、知觉和经验、空间的心理矛盾,这些统称为“现象区”的元素正是王怡画面中的现象总和。比如画面的“细部与声音”,王怡力学轻重结合提高音乐振荡的效果——“作为现象镜头的水”可以引出王怡另一件作品《念》,《念》令我想起村上春树两卷本长篇小说《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上卷为“ 念头显露篇”,下卷为“隐喻改变篇”。——王怡说出了建筑力学的隐喻或象征:“作品《念》为了表现一种‘念’所带来的纠结的心理状态,把原本有重力的不锈钢剪刀,加以细绳的悬挂力和水的浮力,使之与自身重力抗衡。在黑暗的色调下表现了‘念’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她营造的“知觉氛围”一如在霍尔的实践中一种需要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他的建筑是依据场地所有的内涵而设计的, 建筑与场地相融合又达到超越物理的要求,而王怡的画超越了物理学本身。水的浮力、建筑的重力和建筑间的桥式悬挂连接是霍尔重要的构成,“时间困在水上”是成都来福士广场的意境,霍尔触及了时间的神秘性,他看到水时总会反思,他认为用水来体现时间容易给人带来思考。一如泰勒斯一度曾认为“一切东西,实际上都是水。”他这样形容水:“只能片刻拥有,下一秒就是未来;时间很珍贵,你却抓不住摸不到。”如水光阴,稍纵即流逝,霍尔刻意把“时间困在水上”引起人们的“念”,一如王怡的《念》把剪刀困在时间与水中,成为给时间的肖像倒模的布上雕塑。王怡定格静物的《念》可以看作是她早期定格人物的《时光》的转译,把人物化、抽象化的转译。王怡的《念》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克服信息给知觉建筑空间造成障碍的隐喻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霍尔所说的:”为了提升这些隐藏的经验,我们必须刺透大众媒体的光环与面纱。我们必须建立防御系统, 以抵抗成体系的娱乐活动,包括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现在一切可触摸的事物都会获得注意力。如果媒体使我们成为空洞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我们必须确立自己作为’有意识 ’的牢固地位。”《念》一如康定斯基念念于在绘画创作里重造小说家,诗哲者营造的风景。《念》提醒当代人要成为一把有独立意识的剪刀,聚焦自我的定格就是王怡的剪辑。剪辑是拍摄的一次再创造,而架上定格是再造的经典化倾向(Classical tendency)。